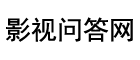在互联网上传播的Lisa参演疯马秀的宣传图片。(图/网络截图)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晏非
不是情色资本,而是情色商品
如果不是韩国女团BLACKPINK的成员Lisa最近的新闻,很多人可能从未听过疯马秀(Crazy Horse Paris)。
疯马秀是一家以裸体歌舞秀为代表节目的法国艳舞俱乐部。有人将它戏称为人肉版的马戏团,和真正马戏团不同的是,台上表演的从动物变成了脱衣舞女,作为驯兽师的观众挥舞着金钱的鞭子。
美国导演弗雷德里克?韦斯曼执导的纪录片《疯马歌舞秀》,记录下了疯马秀脱衣舞女在台前与幕后的故事。
在他的镜头中,疯马秀似乎只是一场大型的舞台表演,只不过表演的人是裸露的。也正是因为这部纪录片消解了疯马秀的情色意味,真正需要被批判的事物,也被消解了。
(图/纪录片《疯马歌舞秀》)
提到情色,关注女性主义话题的读者可能会想起“情色资本”的概念。
在《始于极限:女性主义往复书简》一书中,上野千鹤子和铃木凉美有过关于女性性吸引力的讨论。作为曾经从事AV行业的女演员,铃木凉美以亲身经历讲述,她是如何苦于性剥削和内化的男性凝视的。在讨论中,两人都提到了“情色资本”一词。
“情色资本”是由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参照“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创造的概念。凯瑟琳·哈基姆将情色资本列为除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外的第四大个人资产,认为情色资本是女性的一张王牌,提倡女性应当毫无罪恶感地使用自己的情色资本,来换取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其他资本。
哈基姆的观点为支持“脱衣自由”的人们卸下了道德的重负,心安理得地利用自己的性吸引力来进行交换。而上野千鹤子完全批驳这个概念,并认为情色资本这个概念是一种带有误导性的隐喻。
原因便在于,无论是经济资本、文化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其归属者都能拥有它们绝对的所有权,而利用所谓情色资本的女性,能够自行处置自己的身体吗?站在镜头面前的脱衣女郎,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衣,可以决定脱到什么程度吗?这个问题的回答显而易见。因此,情色资本的所有权是否完全属于女性这点是存疑的。
《始于极限》
[日] 上野千鹤子 / [日] 铃木凉美 著
新经典文化 | 新星出版社 2022-09
此外,其他资本可以通过努力积累,而情色资本不仅难以积累,而且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而且,情色资本的评估标准并不客观,在只能被单方面评估的同时,情色资本的评价标准还完全掌握在观看者手上。
与其说是情色资本,不如说是情色商品更为贴切。以他人意志为主导的脱衣舞女在台上做着各类带有情色意味的动作,这和放在超市展示架上明码标价的商品,并无什么本质区别。
(图/《蒂塔·万·提斯疯马秀》)
情色资本之所以被广泛地默许和接受,和社会上对女性之美的过分宣扬脱不了干系。
在以前,对女性的审美凝视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肤白貌美大长腿”。而现在,变成了鼓吹美的多元化:胖可以美,瘦可以美,皮肤黑可以美,有肌肉也可以美。人们的评价标准看似更加丰富、包容了,但实际上仍然囿于“美”的评价体系里,对美的审视和规训变得更加隐蔽。
听着“你本来就很美”的宣传语,从来没有人停下来想一想,不是物品的人类,为什么需要观赏性的美呢?又为何,没有人对男性说“你本来就很美/帅”之类的话呢?
脱衣舞的“专业性”
是性剥削最好的掩饰
在这场风波之中,一种褒扬的声音以强调脱衣舞的艺术性和专业性的方式呈现。支持者强调跳舞时脱衣舞女展现的肌肉美、线条美,着重宣扬她们在舞蹈上的专业水准。
这种浮于表面的粉饰,实际上巧妙地回避了核心问题,即用所谓的专业性和艺术性掩盖这类色情秀对女性的隐性剥削和内化凝视。
如上野千鹤子对铃木凉美的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作出的尖锐批评:“就好像对春宫图的研究越是‘高深’,就越是沉迷于对外围符号(如外表与衣着)的分析一样。画面呈现的明明是性事,但那样分析就可以对性避而不谈了。”
(图/《蒂塔·万·提斯疯马秀》)
这里并非否认女性在日常有穿衣自由,而是驳斥这类转移主要矛盾的说法。在一般情况下,女性可以作为自己的主体,自行决定自己的穿着。但当身处情色表演的舞台时,即便衣物是女性自行脱下的,也无法否认隐形的社会力量的影响。
变幻的舞台灯光、曼妙的身材、浪漫的音乐,无论这些外在要素让这场表演看上去有多么的“高级”,究其根本,疯马秀还是以刺激观众原始感官和欲望为目的的情色表演,女性的身体在其中沦为一种被观赏的符号。
疯马秀的参演人员。(图/@remidesclaux 摄)
而这种情色表演,本质上是建立在性剥削之上的。一些观众之所以能将其称之为“艺术”,是因为它将自己包装成了艺术的样子。而那些身处更底层的、被困在性行业无法脱身的女性,她们所经历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苦难和折磨,绝非轻飘飘的“艺术”两字能概括的。
什么是更值得活的世界
面对Lisa将在疯马秀表演引起的巨大争议,疯马秀的品牌经理的回应直言,邀请Lisa表演也是为了吸引年轻的女性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我们(疯马秀)未来的观众,因为疯马秀已经成为一个骄傲的、自由女性的象征”。
在互联网上,有关Lisa参演疯马秀的报道。(图/网络截图)
“自由”一词让人回想起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时,罗兰夫人因反对雅各宾派被送上断头台,临行前,她在自由女神像前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随着时间推移,观念日新月异,“自由”一词也频频出现在热点事件的讨论场域中,它时常被用来作为刺向对方辩友的有力武器、捍卫己方拥有做某事的权利的观点。
在这次的Lisa出演疯马秀的事件中,亦有不少人用自由的名义为Lisa辩论,称这是脱衣的自由,是女性展示身体的自由。殊不知,这种自以为的自由意志也是被塑造的。
疯马秀的参演人员正在化妆。(图/ @MichelDierickx 摄)“如果我完全没有强迫你,并使你处于完全自由的状态,你却依然选择了我为你预设的道路,那就是我开始运用权力之时。”福柯道破了社会权力运行的机制,它潜藏在社会网络上的每一个角落。
过于高估自身对自由意志的掌握程度,实际上便忽视了社会权力的潜在控制和影响——当女性站在脱衣舞舞台上,自认为自由地褪去衣物,最乐见其成的是谁呢?
在所谓自由的框架下,一切被压迫的痛苦都可以被轻易抹去。
反映18世纪法国现实社会的小说《悲惨世界》里,芳汀被贪得无厌的泰纳迪夫妇欺骗,为养育女儿珂赛特,卖了自己的头发和门牙,走投无路后迫不得已成为妓女。
而现实世界中,亦有不少从事色情行业的女性是迫于生活压力,不得已而进入这个圈子。
美国歌手Cardi B在节目中回忆以前当脱衣舞女时的经历。(图/网络截图)
美国歌手Cardi B曾因家庭贫困,出于谋生的需求而成为一名脱衣舞女。在成名后的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起曾经的这段经历:“我以前想的是,我是多么让我的父母蒙羞,跳大腿舞的时候,爸爸妈妈的样子就会浮现在脑海里,我感到自己已经没有自尊了。”
Cardi B坦言,虽然这个职业改善了她当时窘迫的生活,但她在开始的几个月感到非常羞愧,也并不鼓励年轻女性去从事这一行业。因此,即便有个别从脱衣舞女转型为国际巨星的成功案例,也不应否认色情行业所制造的痛苦。
部分女性为生计所迫而从事性行业,而此时,一个在年轻人中间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女明星,却主动地走到主要为男性凝视而服务的舞台上,接受他们对一个玩物的审视。
BLACKPINK 2021年线上演唱会。(图/网络截图)
截至2023年8月28日,K-pop女团BLACKPINK仍是全球YouTube上订阅人数最多的音乐类账号,粉丝数量达到了9100万。在此之前,许多人从未听过疯马秀这类脱衣舞秀,经此事件之后,人们开始了解到这类情色秀,其中不乏喜爱该女团和该明星的未成年人。在某社交平台上,甚至已有网友通过发布裸露自身的照片,来为出演疯马秀的Lisa“应援”。
作为世界级的偶像明星,Lisa参加疯马秀的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她个人身上,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后续反应。喜爱Lisa的粉丝可能会因此逐渐接受将自己身体客体化为观赏物的想法,更无负担地夸赞“情色资本”,更能接受用自己的身体来换取福利。
在一个性压抑、性保守的社会文化中,女性曾经努力将自己的身体从压抑中解放出来,用了数百年时间推动性观念的解放。而今天,对女性的凝视披上了消费主义和审美自由的外衣,取代了宗教和传统道德对女性显而易见的控制。此时,如果被“自由”蒙蔽了双眼,只会使性压迫和性剥削行使得更加隐蔽和顺利。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位具有国际级影响力的女团成员参加脱衣舞夜总会表演的行为?这似乎可以以铃木凉美在书信中的诘问作为结尾:
怎么做才能把一个更值得活的世界交给妹妹们?是进行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继续鼓吹向下的自由?还是保持清醒的头脑,铭记曾受到压迫和剥削的她们的痛苦?答案不辩自明。